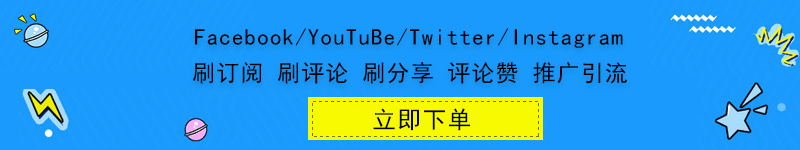加密货币的历史不长,但却绝对令人兴奋,因为它迅速改变了世界。行业的迅猛发展,吸引了大量机构和个人投资者入局,风险也随之相伴。基于对加密行业的深入了解研究,我们认为投资者应关注如下重点问题:
(一)加密货币案件的可诉性
目前,各国对加密货币的法律性质并不统一,可能将其认定为证券、商品或货币[10]。出于监管和保护需要,大多数国家均承认加密货币的财产属性,这也是与之相关案件的可诉性前提。
以中美欧为代表的主流国家中,随着对加密货币财产属性认可度的变化,中国经历了从有限保护,到认定无效再到不予受理的过程。以2021年中国人民银行等十部门联合发布的《9.15通知》为界,此后多数法院尽管仍倾向于受理加密货币有关争议,但公开查询[11]的数据显示不予受理的比例已达3成且呈上升趋势。驳回起诉的理由,除涉及刑事案件直接采用“先刑后民”外,主要是基于《9.15通知》中的“违背公序良俗”及“缺乏合法经济评价标准”[12]。同时,我国大部分法院以“没有法律规定”为由不支持加密货币的利息求偿权,仅在《9.15通知》出台前的极个别案例[13]中,基于加密货币的经济价值,法院参照民间借贷利率计算方式支持了原告的利息请求。整体上,随着财产属性的日渐丧失,加密货币案件的可诉性在中国正变得越发艰难。而与之相对的是,在欧美的司法趋势中,出于保护投资者权益之目的,相关案件的可诉性正日渐加强。
建议:谨慎选择投资策略,了解不同国家的具体法律规定,确保合规性和可诉性。在大环境诉讼不利的情况下,国内投资者还可考虑提前选择仲裁作为争议解决方式。限于仲裁的保密性,目前能查询到的裁决不多,主要以北京仲裁委员会(“北仲”)为主。在深圳仲裁委员会作出的首例承认比特币为财产的裁决[14]于2020年4月被深圳市中院以违反公共利益为由撤销[15]以后,北仲依然在2022年4月14日的一起委托管理比特币纠纷案中裁定认为比特币等虚拟货币为受法律保护的虚拟资产,且明确表示目前我国并无法律和行政法规禁止虚拟货币和以虚拟货币为标的的交易活动。从北仲的裁定倾向来看,与诉讼相比,仲裁可能是涉及加密货币纠纷的更优选择。因此,对发生在中国的加密货币纠纷可优先考虑在签约时约定仲裁方式。
(二)管辖权确定之困境
加密货币可诉后,就会面临管辖权如何实施的问题。区块链技术的去中心化,导致其天然的跨境属性。从法律角度来看,加密货币的去中心化与属地管辖的地理依赖相违背,匿名性亦与各国在民事诉讼中普遍确立的被告人明确性之要求冲突,加之网络交易的独特性,导致识别被告的过程复杂,从而为各司法管辖区确定和实施加密货币跨境案件的管辖权带来了困难。2021年5月,因币安技术故障导致投资者上亿美元损失所引发的管辖困难,就是一个例证[16]。
管辖权问题在中国因其可诉性变低而并不明显,从英美的最新案例来看,长臂管辖和对核心法律概念的突破性解释为此类管辖权困境带来了曙光。在美国纽约州南区联邦法院阿里巴巴诉阿里巴巴币基金会(Alibaba Group Holding Limited v. Alibabacoin Foundation[17])一案中,阿里巴巴历经艰难举证[18],使法院认定购买加密货币的行为发生在纽约州内,从而对该案享有管辖权。英国高院在审理Ion Sciences vs Persons Unknown一案中,通过对“明确”作出扩大解释,以公钥实际控制人、电子钱包所有人等信息的明确为标准,向“明确”的被告人下达资产冻结令,而获得管辖权。在可预期的时间内,管辖权问题会是贯穿加密案件始终的一个痛点,同时也是投资者诉权真正的起点。随着相关判例的增加和立法进程的推动,相信该问题会逐步得到解决。
建议:关注不同国家的法律和裁判倾向,不可一概而论。管辖权通常属于法定问题,但由于加密货币的涉外性、法律的滞后性和差异性,造成了现实困境。如需突破在诉讼或仲裁中遇到管辖权难题,不仅需要法官的配合,更需要高超的诉讼技巧,建议寻求专业律师的帮助。
(三)不同投资行为的法律关系认定及后果
与加密货币投资有关的民事法律行为分为有效和无效两类。在有效前提下,不同行为可能被认定为不同的法律关系。于加密货币发行环节,以美国为首的很多国家倾向于将其认定为证券行为,从而在《1933年证券法》框架下对投资者进行保护;投资者之间则可能构成买卖/转让、借贷、委托关系(如代为理财)、投资关系(如购入基金)等,主要受合同法约束,部分时候适用侵权法;而投资者与交易所、服务商等中介机构之间的法律关系,从欧美现行案例来看,多会被认定为委托或信托关系,不同关系会影响到加密货币在中介机构破产时的定性问题[19]进行影响到投资者权益。
从投资者保护的角度而言,无效法律行为引发的后果更为严重。尽管无效认定尚存争议,但从裁判结果来看,中国趋向于将与加密货币有关的绝大多数行为认定为无效,并要求投资者“自担损失”[20]。目前无效认定的范围主要包括加密货币的发行融资行为,挖矿,在平台及普通投资者之间的买卖、借贷、委托投资、返还纠纷等,《9.15通知》出台以后,还延伸至了“矿机”买卖[21]等附属行为。而欧美对于加密货币的投资大多采取有效+保护的态度,但仍存在无效认定的可能性。按照美国纽约州法和英国法的规定,与未成年人签署的合同可由未成年人自行决定无效。考虑到区块链技术的匿名性,加密货币的交易风险将因此而增加。
建议:重视合同签署,明确法律关系。因加密货币行业尚在起步阶段,参与者对合同文件的重视度不够,往往会导致投资行为的无法或不利定性。同时,对于投资行为法律关系的不同认定,会导致不同的请求权基础(基于合同、物权还是不当得利),从而对投资者权益保护路径和结果产生实质性影响。因此,建议投资者选择最有利于权益保护的投资行为并签署合同。
(四)投资损失之救济路径
2022年5月,算法稳定币TerraUSD(UST)和Luna的崩盘导致了行业海啸和投资者的巨额损失。6月13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区针对交易平台Binance. US推广并出售UST和Luna提起了集体诉讼,称该交易所非法出售未注册证券,并错误地将其描述为“安全”和“有法币支持”。此举再次引发投资者对损失救济问题的关注和担忧。事实上,加密货币因其行业特性和技术缺陷,投资过程中存在技术故障、被诈骗、交易平台侵吞资产、黑客攻击等诸多风险,因此遭受损失后如能正确救济,对投资人的权益保护至关重要。目前,关于投资者的损失赔偿责任主要源自合同义务之内的违约责任和之外的侵权责任。民事案件中的被告以代码开发人员和中介机构为主,后者是被诉最多的主体,且目前各国司法机关对于中介机构的安保义务和赔偿责任认定有向传统银行靠拢的扩大化趋势。
1.对代码开发人员/开发商进行索赔
此类索赔通常基于侵权行为,出现在代码运行错误导致用户损失的过失侵权案件中。该等赔偿义务通常以存在注意义务和疏忽为前提条件,而注意义务无论在普通法还是大陆法中都是一个非常复杂和抽象的概念,由法院在每个具体案件中进行评估。英国高院在2022年的Tulip Trading v Bitcoin Association [2022] EWHC 667 (Ch)案中,就驳回了原告提出的开发商负有注意或信托义务,应恢复其被黑客剥夺的私钥和帐户访问权限之请求。出于对代码开发人员/开发商承担该类责任的公平性和严格责任制度的考量,目前支持此类索赔的案例极其少见。
2.针对交易平台等中介机构的索赔
绝大多数的加密货币投资行为都会与交易平台等中介机构产生链接。频繁遭受黑客攻击、故障、欺诈用户和擅自行动(如Luna崩盘后币安等交易所自行决定暂停用户提现)的交易平台,是监管和诉讼的重灾区。MiCA法案所引领的监管趋势明确了中介机构的托管义务,从而延伸出中介机构对客户资产的隔离和赔付责任。据此,如中介机构破产,投资者的加密货币将不属于破产财产(除非交易所如美国SEC要求的那样将托管财产并入交易所的资产负债表,此种情形下客户只能在交易所破产时享有一般债权,无法行使取回权),同时对于因技术或黑客攻击而导致的损失将由中介机构承担。
在关于交易平台/服务商等中介机构的诉讼及仲裁中,侵权(含证券诉讼)与违约都是可能出现的理由。中介机构安保义务和赔偿责任的扩大往往以法院对其提供的单方免责声明和仲裁等格式条款的否认为前提。理由是此类条款可能减损用户权力,改变合同中的平衡关系,有违公平原则。2022年4月,Coinbase就在Bielski v Coinbase加密货币被盗案中,被美国北加州地区法院剥夺了强制仲裁资格。
建议:选择合适的中介机构。结合案例及实践,我们总结了挑选中介机构的重要指标:已获得的许可和资质、募集说明书等发行文件、代币的结构及技术、对重要信息的披露、司法辖区、过往信誉、交易政策和程序(含中断和暂停)、资产托管情况、代币升值的收益分配规则、审计机构、运行透明度、内控制度、隐私与洗钱、清算制度、已缴纳准备金以及购入保险等。需提示的是,Coinbase等大型交易所,均已增加了保险措施,这是因为平台在面临网络攻击时,会造成暂持的加密货币损失甚至破产,仅靠事先向监管部门缴纳的准备金和担保难以弥补。因此购入保险,可形成有益补充。
(五)加密货币的执行困境
加密货币特性所导致的执行难是全球司法实践中的难题,目前鲜有成功案例。加密货币支付需要所有者的私钥验证方能完成交易,私钥存在被债务人自身保管或被中介机构保管两种情形。
当私钥被债务人自身保管时,无论法院如何判决,均需要持有人的配合,否则加密货币无法实际上被强制执行。在(2020)苏09刑终488号一案中,PlusToken的负责人就在被抓获后依然通过钱包APP的闪兑功能转移隐匿了价值约1.5亿元人民币的加密货币,而法院对此束手无策。实践中,法院在加密货币被委托代持的情况下可通过交易平台的协助进行相关查封、冻结或执行。不过目前我国涉案的交易平台中,出于合法性原因,平台均由外国企业运营,并实际为海外公司,所以经常会出现无有效通讯地址的情形,从而导致协助执行通知无法送达。而在海外的执行案件中,交易平台也经常存在跨境注册及运营的情况,执行情况较之中国并无太多优势。
建议:权利人在主张加密货币交付的同时,可一并提出金钱赔偿作为替代履行方案。但加密货币价格波动极大,难以通过评估的方式确定财产价值,同时我国严禁加密货币和法定货币兑换,也不存在合法的加密货币交易场所。因此,原则上需双方当事人对具体金额达成一致或提前明确约定,方能形成有效的替代方案。